奇特的甘肃古长城
奇特的甘肃古长城
侯丕勋
华夏先祖,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发明了筑城技术。在其后四千多年历史中,我们的祖先又以无与伦比的创造精神,把筑城技术发展到了奇、特、绝的程度,并曾运用这些技术 修筑了无 数坚固而壮丽的“居城”和雄伟而奇特的“塞城”。“居城”成了帝王治国平天下的中心和民众的居住之所,而“塞城”则被作为历代王朝御敌安边的人工屏障。
数坚固而壮丽的“居城”和雄伟而奇特的“塞城”。“居城”成了帝王治国平天下的中心和民众的居住之所,而“塞城”则被作为历代王朝御敌安边的人工屏障。
古代甘肃,地处西北边疆,战略地位极为重要,历来是关中的天然屏障,与关中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。所以古人有言:“欲保关中,先固陇右”(《读史方舆纪要·巩昌府》)“欲保秦陇,必固河西”(《读史方舆纪要·甘肃镇》)。然而,作为关中西北天然屏障的古代甘肃,对关中的护卫作用实际上是有限的,它并不能确保关中地区不受边疆少数民族的扰掠。为弥补古代甘肃这一天然屏障对关中护卫作用的不足,从战国秦昭王时开始,就在这里修筑用于军事防御的长城。此后,秦、汉、明各王朝又相继在此地修筑长城。由于受当地地理条件等因素影响,古代甘肃境内的长城形成一种奇特景观。
一、 秦始皇“因河为塞”的西长城
长期以来,每当人们论及秦始皇万里长城问题时,总是先入为主地带有这样一种观念,即万里长城是在地面上人工夯筑而成的、绵延不绝的高大城墙。其实,这种观念与史实明显不符,万里长城西段及其首起地尤为如此。据《史记·韩安国列传》记载,蒙恬为秦侵胡时,曾“累石为城,树榆为塞”。可见,蒙恬所筑万里长城西段并非全是城墙绵延不绝的长城。劳干曾著文论及此问题,他说:“秦汉的长城,据记载上说,却不全是城垣,有若干地方是木栅”(《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》,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19本)。
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对秦万里长城西段的特点有着较为详尽的记载:“秦灭六国,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,悉收河南地。因河为塞,筑四十四县城,临河,徙谪戍以充之……起临洮,到辽东万余里。”从司马迁这一记载看,蒙恬当年所筑秦万里长城之西段,是以“因河为塞”、“临河”筑四十四县城和徙民戍守为特征的一段长城。由此看来,当年蒙恬所筑万里长城之西段,是将具有天然防卫作用的黄河作为主要军事屏障,将匈奴容易渡河处所筑四十四县城作为军事据点,然后徙兵民戍守,而三者的主体则是“因河为塞”。
虽然《史记》的记载,没有明确提到北起秦榆中、南至秦临洮(今甘肃岷县)的这段西长城之特点,但可以从“因河为塞”之“河”涵义的扩充方面探知大概。在先秦时期,“河”为黄河的专名,可是到了西汉时期,“河”这个词的涵义开始出现扩充现象。这一时期,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曾经使用的简牍文字中,有着为数不少的“河”字,如“从河水中天田出”(E· P· T68 : 63)、“兰越甲渠当曲陇塞从河”(E· P·T68:73)、“欲还归邑中,夜行迷河河”(E·P·T68:37)、“中夜行迷渡河□”(E·P·T68 : 47)、“隧南天田夹河,还入隧南天田”(《合校》231·88)、“第五隧北里所见马迹入河”(E· P·T48:55A)、“河中毋天田”(EJT21·177)。众所周知,黄河干流和支流均未流经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,从而以上简文中之“河”,既不是指黄河干流,也不是指黄河支流,而是指位于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与黄河毫无关系的若干内陆河。足见,作为先秦时期黄河专名的“河”,至西汉时已经变成了西北众多河流的通名。受“河”的涵义扩充的启示,我们认定西汉时人们把洮水叫作“洮河”肯定不会有何不妥。这就是说,首倡万里长城西段“因河为塞”说的司马迁,把秦榆中至秦临洮之间的一段长城也是包括在“因河为塞”的范围之内的。毫无疑问,这一地段内“因河为塞”式长城,是以具有天然屏障作用的洮河、洮河之东的“临洮”城(今岷县城)和狄道城(今临洮城)以及戍边吏卒共同构成。综上所述,由于秦始皇时蒙恬尚未在从河套至“临洮”之间修筑城墙绵延不绝的西长城,所以当地绝不可能有城墙式长城之遗迹。因此,顾颉刚先生等人在秦始皇万里长城首起之地“临洮”(今岷县),找不到万里长城的遗迹则是很自然的。
二、汉长城的附设工程“塞天田”
“塞天田”也称“天田”,是古代长城的附设工程。在敦煌和居延地区所出土的简牍资料中,对附设于汉长城的“塞天田”多有反映。
对“天田”,三国苏林作了如下解释:在塞要下,“以沙布其表,且视其迹,以知匈奴来入,一名天田”(《汉书·晃错传》“中周虎落”注)。其意是说,在险关要塞的通行处地面,利用人工铺设一层细沙,以利边防吏卒白天察看匈奴于前一天夜间入侵塞下时所踩足迹,藉以判断敌情,此谓之“天田”。这一解释虽然较好地把握住了“塞天田”的本质性内涵,但若从当地所出土简牍资料看,其解释仍然不够完善。
“塞天田”大多修造于长城外侧不远处,也有修造于险关要塞之地的。长城外侧之“塞天田”多呈长条形,走向与长城基本平行。有些地段“塞天田”很长,仅边防吏卒“日迹”(戍边吏卒,每日察看“天田”上敌军人马留下的足迹)时,有的就曾“日迹”23里(E·P·T51 : 411)、有的“日迹”45.5里80步(敦煌汉简1707)。“塞天田”宽度,似无定制,一般宽约3米左右。
修造“塞天田”的活动,一般在长城修筑完成之后进行。修造时,先用锄头一类工具,在长城外侧不远处地面,平整出一条走向大体与长城平行、宽约3米的平坦条带,然后在条带上铺上一层细沙(无沙处可以铺上细土),并用“木杖”和“杖”一类工具抹平,至此,某一地段的“塞天田”就算修造完成了。这种修造“塞天田”的活动,因主要使用“鉏”,故简文称为“鉏治”天田(《流沙》戍役30、敦煌汉简1552等)。
修造“塞天田”,其目的主要是用来察看入侵敌军人马留在“塞天田”上足迹的多少,藉此判断敌情, 以便采取相应的御敌措施。可是,一旦敌军人马在“塞天田”的某些段落踩上足迹,从此这段“塞天田”便丧失侦迹作用。若要使这段“塞天田”继续发挥侦迹作用,那就要按边防机关的规定,每天派出吏卒进行“日迹”,并用“木杖”等工具,将敌军人马所踩足迹处疏松、抹平,恢复“塞天田”的原貌。这种活动,简文称之为“画天田”(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上203·29A、《流沙》戍役30)。
戍防吏卒巡视“塞天田”和“画天田”情况,均按参加人员身份,一律以“月”为时间单位分别记录成册。这种记录“日迹”而形成的簿册,简文称作“日迹簿”(E·P·T53 :38、E·P·T58:105、E· P·T58:92)。戍边吏卒每月的“日迹簿”记录稿完成后,要按规定清抄一份,然后将两种“日迹簿”分别进行密封,最后将记录稿保存于本烽燧,而将清抄本报送上级机关备查。据此不仅可以看出,位于河西走廊汉长城沿线的戍边制度的严密,而且可以看出当地长城及其附设工程“塞天田”所独具的特点。
三、河西走廊的“壕沟城”、“河中城”与“夹壁城”
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和《明史》中,对河西走廊长城的记载均颇疏略,据之难以具体了解当地长城的实际情况。通过近年来的实地考察和对有关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研究,大家才对汉、明两代在河西走廊因地制宜地兴修“壕沟城”、“河中城”与“夹壁城”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。
元鼎六年(前111),西汉在今甘肃山丹县县境内修筑的长城,据实测全长98.5公里。这段长城“由壕沟、壕棱、自然河、烽燧、列障构成”,部分段落“以壕沟代替墙垣”,“现存壕沟深0.8一3米,口宽5一8米不等;壕沟里沿有壕棱,呈土脊状”;“现存壕沟全线共59.95公里”。在龙首山各山口也掘有用来防御敌人的壕沟(《山丹县志·文物古迹》)。
西汉在此地人工所掘“壕沟城,呈西北—东南走向,位于明长城北侧不远处。它是用以防御来自北面的匈奴,所以在掘壕沟时,将壕沟北壁掘成垂直状,从沟中所掘之土,堆放在壕沟南沿,形成一条土脊。在壕沟南沿土脊上修筑的烽燧突兀而起,雄伟壮观。
河西走廊地区的汉、明长城,每当跨越干河道(季节性河流河道和旧河道)和有水河道时,既不能又无法在河道中夯筑土城墙,同时也不能挖掘成壕沟。这样,因河道阻隔而造成的城墙的中断,就给少数民族入侵长城之内留下了通道。长城的这一重要缺陷,势必导致其御敌作用的降低以至丧失。然而,汉、明王朝当时就曾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。
据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释文称:吏卒“□所持木杖画灭迹,复越水门”(336·32)。这是说,居延某地戍边吏卒的营房位于长城之内,当他们去长城之外画灭“天田”上敌军足迹时,由于长城上无通向长城之外的道路,于是就从河道中的“水门”出去,当完成“画天田”任务之后,又从河道中“水门”返回营房。很明显,居延汉简“复越水门”简文,正好是居延地区河道中修建有长城的重要文证。
当然,河西走廊地区河道中修建长城一事,并非只有孤证。从上述记载已确知,汉代河西走廊地区,凡有长城之地就会有“天田”,而有“天田”之地也就有长城。正因如此,所以居延汉简中“水中天田出案,常等持禁物兰越塞”(E·P·T68:74)和“兰越甲渠当曲坠塞,从河水中天田出□,案常持禁物”(E·P·T68 : 63)简文表明,当地有水河道中的部分地方曾修治有“天田”。河道中既然存在“天田”,那就意味着河道中也修建有长城。这种长城就是汉代河西走廊的“河中城”。
然而,汉代河西走廊地区的“河中城”的样式、结构、建筑材料及所存在地区等,尚缺乏可供研究的具体材料。不过,从简文中“复越水门”和河西地区曾修建过“虎落”、“强落”(即用木料修建的用来御敌的木栅栏)的史实可以得知,河西地区“河中城”是用木料所建成的“栅栏式”长城。这种建在无水或有水河道中的栅栏式长城,既把河两岸用土夯筑的长城连接成了整体、堵住了河道中的长城缺口,又因留有“水门”,从而便利了戍边吏卒往返长城内外的戍边活动。同时,这样的栅栏式“河中城”,既不能被流量不大的河水所冲毁,又可起到很好的御敌作用。可见,“河中城”是古代人在河西走廊地区创造的一种特殊的长城景观。
河西走廊地区的明长城,修筑时间较晚,至今仍有若干段落城墙保存较为完好。这自然为考察明长城原有特点提供了条件。1994年6月21日,我们在今山丹县县城东5公里多的壕北滩(位于312国道南、山丹焦化厂东南)考察明长城时,曾发现一段特殊的“夹壁”长城遗存。所谓“夹壁”,是说这段长城是由并列的、相互存在一定距离的两堵城墙共同构成“夹壁”状。这段“夹壁”长城,与明长城主城的一段共同构成。明长城主城,自312国道之南不远处向东南延伸(偏角约30º),并南跨山丹河河道,在河南二级阶地上与副城构成并列状。主城位于西南面,而副城位于东北面。据实测,主城最高处3.5米,副城最高处1.1米;主城基厚2米,副城基厚0.7米;主、副二城墙间距2米。明“夹壁”长城残长10米左右,其余段落副城已毁,现呈土梁状,主、副二城之间状似沟渠。从主、副二城墙间距离看,其宽度已达到可供通行的程度,似乎表明,这可能是一段“夹道”长城。另在居延地区考古发掘中,曾发现有一种所谓“双重塞墙”,“从痕迹看,是两道平行的相距3—5米的低垅。其中内侧的一道,疑是塞墙,中间为天田,外侧的可能是天田边缘的低垣。”(初师宾《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》,《汉简研究文集》第195页)从并非仅见的“夹壁”长城遗存,可知这也是一种修筑在重要边防地段的特殊长城。
四、明长城西部终端的弧状长城
明长城西端,传统说法认为在嘉峪关关城西南讨赖河(今北大河)北岸上。这种观点表明,明长城的西端是一个点。对这种说法,学术界向来无异议。不过,根据我们1994年6月7日的实地考察和有关方志资料记载,嘉峪关关城大体位于走廊中部稍偏南的地方,而明长城终端的一段,从关城外墙下西南角向西南方延伸至北大河北岸上,“长6559米”;另一段从关城外北墙下“闸门墩”先向东北再折向西北延伸,且直达黑山之腰,“长8200米”。据当地文物部门实测,从北大河北岸直至黑山之腰的两段长城,共长14759米(《嘉峪关市文物志》第3页)。很明显,明朝当年曾把长城西部终端筑成了以嘉峪关城为中心,南连讨赖河北岸、北达黑山之腰,弧口向西的弧状城墙。明朝如此修筑长城西端的目的,无疑在于封闭整个走廊西部,以利防御西域少数民族政权对河西的扰掠。据此,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,明长城西部终端不是讨赖河北岸上的一个点,而实际上是以嘉峪关关城为中心,南连讨赖河、北连黑山,长为14759米的一段弧状墙。
文章出处: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 1997年第3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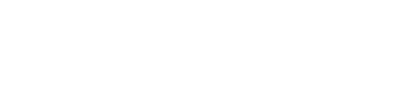



 甘公网安备62112602000034号
甘公网安备62112602000034号